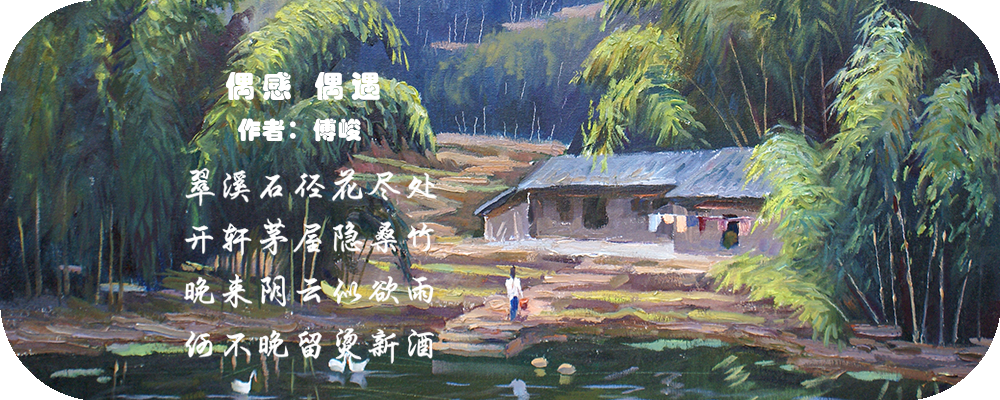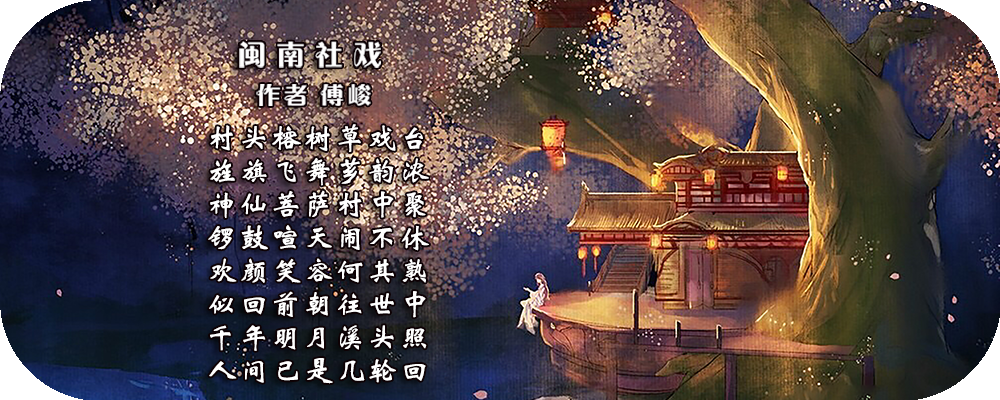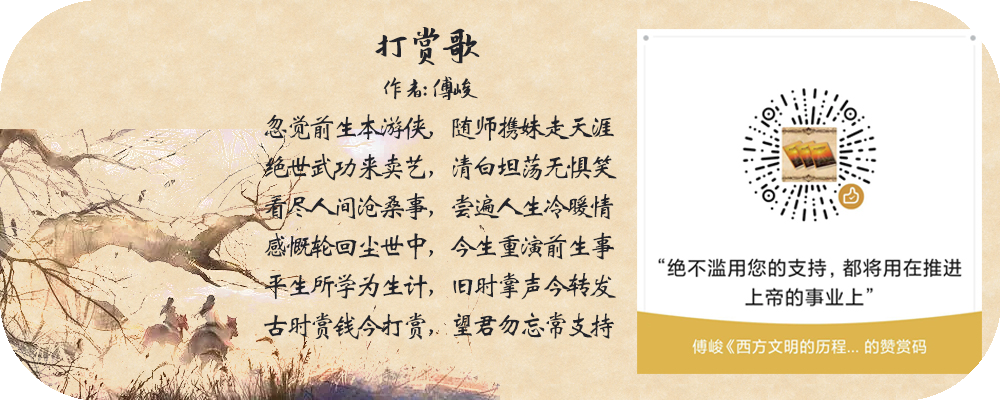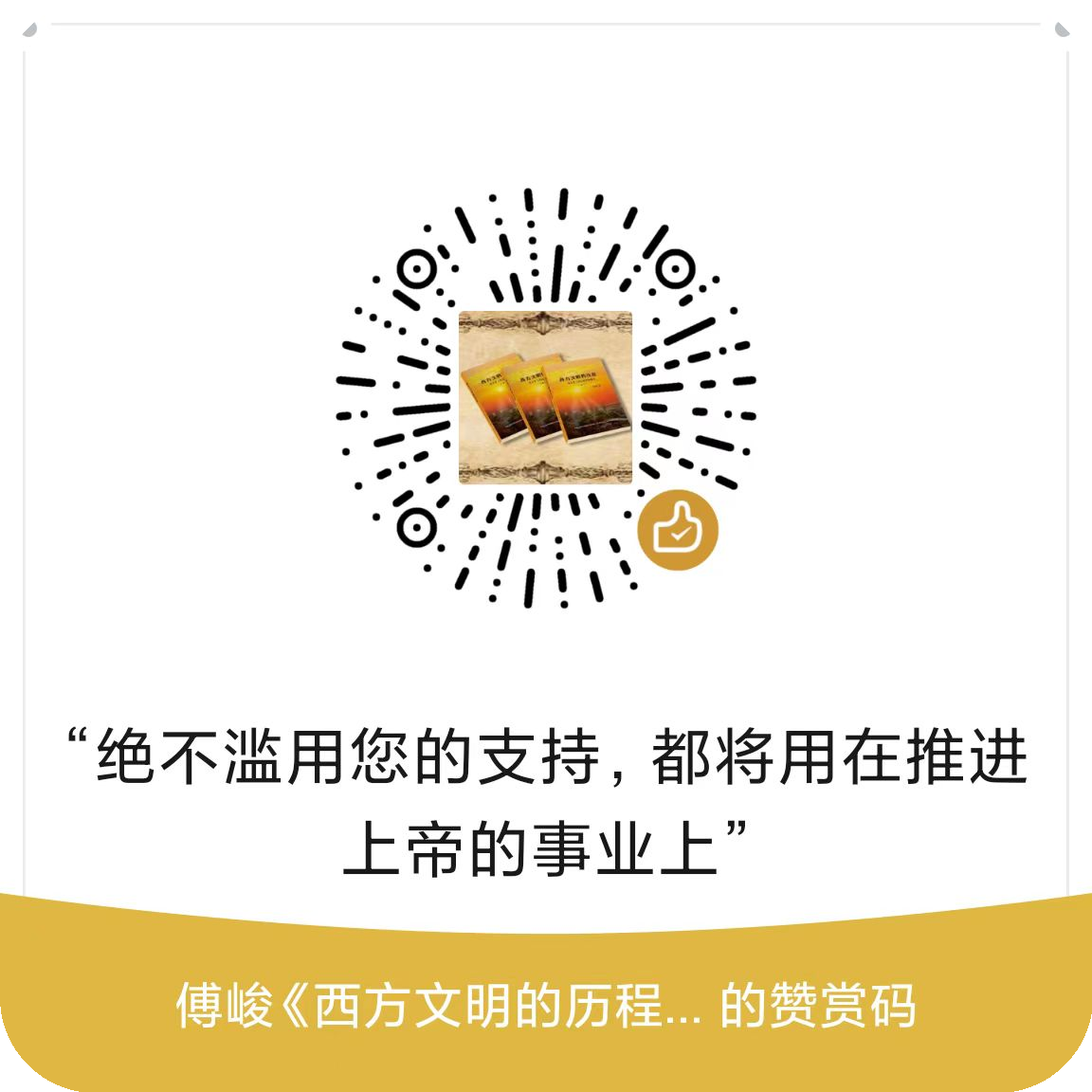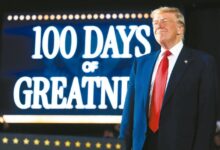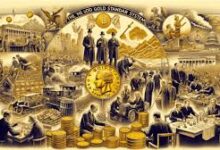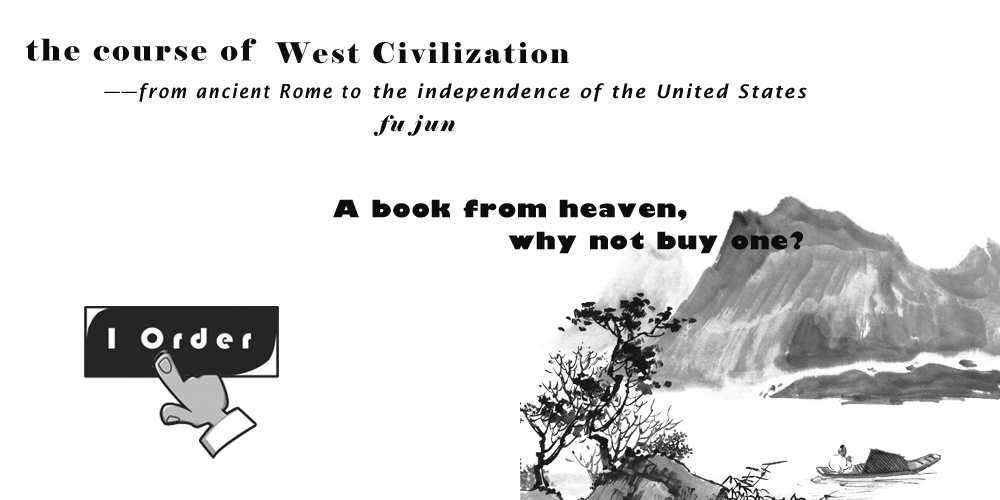近几日,互联网上流传许多有关叙利亚新政权HTS的消息,这个所谓的”新政权”实际上是一个恐怖组织。他们在叙利亚沿海地带对阿拉维教派和基督徒展开血腥屠杀,触目惊心的图片传遍了全世界,让当初热烈庆祝阿萨德独裁政权倒台的人陷入尴尬的沉默,这些当初满怀对自由民主渴望的人们,曾坚定地相信,只要阿萨德的独裁统治被推翻,叙利亚就会迎来民主自由的春天,欣欣向荣的未来,然而,如今血腥的事实击碎了这种美好的愿景。
叙利亚当前的混乱与悲剧,并非简单的政权更替问题,而深刻地揭示了一个历史真相:宗教决定历史进程。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够逐渐发展出稳定的民主自由制度,根本原因在于其扎根于基督教这个深厚的土壤之上,自由与民主并非可以任意移植的抽象概念,它们需要特定的精神土壤和文化环境才能真正生根发芽,脱离了基督教背景,自由民主制度往往会迅速凋零枯萎,甚至变形为专制与暴力。纵观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,不难发现基督教不仅塑造了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观,而且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社会的政治结构与制度设计。正如我在《西方文明历程》一书所强调的那样,宗教决定历史,基督教决定西方历史,自由民主只有在基督教世界才可能实现。其实无论是伊斯兰还是基督教世界,对经书的不同理解必然形成不同的教派,但是基督教不同教派之间虽然也存在分歧与争斗,却能在基督教的基本原则——兄弟之爱的基础上最终形成大融合,尤其在蛮荒的新大陆北美,这种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,也成就了美国的统一与强大,并衍生了它的副产物,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。

与其他宗教或者没有神论的人类社会相比,伊斯兰世界与民主自由最为绝缘,最为格格不入。这种现象并非偶然,伊斯兰教奉行的是《可兰经》,而这本经书中的诸多教义本质上与自由民主背道而驰,最主要是可兰经强调政教合一模式,即国家即教会、教会即国家,也即宗教与政治权力高度统一的,必然形成与自由民主截然不同的治理结构。其次,伊斯兰人强调《古兰经》的绝对权威和不可更改性,不同教派对经文的解释往往导致不可调和的分歧,这一刚性原则很容易造成对立与分裂,更不用说形成建立在兄弟之爱基础上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,所以伊斯兰教派间的分裂不仅难以融合,反而日益深化为更深刻的冲突,实际上,纵观伊斯兰历史,从未真正孕育出稳定的自由民主政体,即使有短暂的尝试,也很快因教派分裂及冲突而陷入混乱。
此外,伊斯兰教早期即与政治权力结合,先知穆罕默德既是宗教领袖,也是政治统帅,国王,这种传统使得教派分歧直接演变为国家间的对立。中东地区的地理 和部落社会结构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,使得教派认同与国家认同高度重合。公元632年,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,伊斯兰社会因继承问题分裂为两大派系:逊尼派和什叶派。这一分裂不仅是一场宗教争议,更是一场政治权力的争夺。逊尼派主张通过选举产生哈里发,而什叶派则坚持哈里发的继承应限于穆罕默德的血脉,即阿里及其后裔。这种分歧在公元661年阿里被刺杀及680年侯赛因在卡尔巴拉战役中殉难后进一步加剧,最终形成了不可弥合的教派对立。
从那时起,教派的分裂便与国家的形成紧密相连。例如,什叶派在伊朗地区的崛起可以追溯到16世纪初,当时萨法维王朝(1501-1736年)将什叶派确立为国教,以对抗奥斯曼帝国的逊尼派霸权,这一举措不仅巩固了伊朗的民族认同,也奠定了其作为什叶派大国地位的基础。与此同时,奥斯曼帝国则以逊尼派为正统,统治着包括叙利亚、伊拉克和阿拉伯半岛在内的广大地区。这种教派与国家的结合模式在中东历史上反复出现,成为其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。于是在当今的伊斯兰世界,不同的教派往往成为国家身份的核心,教派往往直接对应国家,国家也成为教派的延伸,教派冲突直接体现为国家之间的对立。我们可以发现,无论是小国如也门、卡塔尔,阿曼,叙利亚等,还是大国如伊朗、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等,教派与国家的界限几乎重合。沙特阿拉伯对应着逊尼派这个大教派,伊朗对应着另一个大教派,什叶派,这种现象比较明显且上面也分析过,我们就不再继续讨论了。我们接下来将深入分析也门、卡塔尔,阿曼,叙利亚这些小教派即国家的实例,应该更能看到教派即国家这种伊斯兰世界特有的现象。

也门的宗教格局以宰德派(Zaydi Shiism)为核心,这一什叶派分支在也门北部山区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。宰德派起源于8世纪,因其对哈里发继承权的独特主张而自成一派。从公元897年起,宰德派伊玛目在也门建立了独立政权,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20世纪。1962年,也门北部的宰德派君主制被推翻,但其宗教影响力并未消散。近年来,胡塞武装(Houthi Movement)作为宰德派的代表再度崛起,与逊尼派主导的中央政府及沙特阿拉伯支持的势力展开激烈对抗。也门的教派冲突本质上是国家内部权力斗争的缩影,宰德派不仅是一种宗教认同,更是一种政治实体的象征。
卡塔尔是由瓦哈比派形成的国家,瓦哈比派是逊尼派内的一个小派别,强调严格遵循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理念,倡导严格的宗教生活方式,在卡塔尔,瓦哈比派的思想和教义被广泛接受并得到官方的支持,其教义主导着宗教、教育、司法等多个领域,对社会具有绝对的影响力。因此,可以说卡塔尔实际上是一个以瓦哈比派为宗教基础而形成的国家。
阿曼是世界上唯一以伊巴德派为主体的国家。伊巴德派是逊尼派和什叶派之外的第三大教派,历史悠久,起源于早期伊斯兰时期,具有鲜明的宗教特色和独特的教义体系。与逊尼派和什叶派相比,伊巴德派主张相对温和、宽容的宗教态度,更强调个人修行、和平共处与社会稳定。这种教派特色深刻地塑造了阿曼独特的社会氛围、文化传统以及政治生活,造就了阿曼在伊斯兰世界中较为温和与包容的国家形象,显著区别于其他以逊尼派或什叶派为主的国家。
约旦,阿富汗也是由小教派形成的国家,由于本人的知识有限,应当还遗漏了不少其他一些小教派国家的实例。其实叙利亚曾经也是由小教派阿拉维派主导的一个国家,而如今它的新政权HIS,实际上是ISIS的一个分支,他们主要信奉的是逊尼派中的极端派别萨拉菲圣战主义(alafi-Jihadism),也是一个小教派。

从上面的分析中,我们应该更加可以看出,在伊斯兰世界,无论是也门、卡塔尔,阿曼这样的小教派国家,还是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大教派国家,宗教与政治的交织塑造了它们类似的命运,相似的道路,也即“教派即国家”这一特有现象。这与基督教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,基督教强调的兄弟之爱、宽恕、个人与上帝直接交流,只有在这基础上才可能形成自由民主的制度,并且促进了社会的多元化和包容性,使不同信仰和文化得以共存,当然我这里再次强调下,这样的社会也必须以基督教为主体,否则必然出现如同拜登时期美国的乱像。而上千年的政治现实与可兰经的政教合一,强调绝对服从于宗教政治权威的教义的多重加持下,伊斯兰教派间却是难以容忍异己,根本就不存在兄弟之爱,甚至是兄弟阋墙,教派的融合极为困难,不同教派的矛盾无法通过自由民主的和平协商手段解决,而是随时付诸于世俗国家的武力,这也正是叙利亚等国家在民主浪潮后迅速陷入教派战争的根本原因,也解释了为何自由民主难以在中东生根的原因。
回顾更早之前的阿拉伯之春时期,许多西方国家和媒体曾为推翻中东地区的独裁政权而欢呼雀跃,认为民主自由的“人间天堂”即将在伊斯兰世界降临。然而,现实却一次次上演着悲剧。那些至今仍未被现实唤醒的,认为民主自由普适于任何社会的理想主义者,或许该从叙利亚的最新悲剧中深刻反思出一些东西。他们应当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观点,脱离了宗教与文化背景的民主移植是无法成功的,宗教和文化传统在社会政治变迁中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。自由民主并非普世价值,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,而是需要特定土壤的特殊制度产物。西方式民主自由的成功,不仅仅是政治设计的成功,更是特定宗教文化长期积累的结果,将民主自由机械地移植到缺乏相应文化和宗教基础的地区,不仅不能带来稳定与繁荣,反而会加剧当地的冲突与混乱。尤其是在伊斯兰世界,仓促引入的民主实践往往被宗教极端势力所利用,造成严重的社会分裂、内战与人道主义灾难。理解这一历史规律,进而找到适合该地区的和平发展道路,或许是解开中东困局的第一步,也许这也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与责任,也是我锲而不舍地推广我《西方文明的历程》这本书的原因所在。

年轻时痴迷于武侠小说,有一个武侠梦,跟着师傅,带着小师妹,行走江湖,浪迹天涯,看尽人生百态,笑纳人间风云,在师傅的呵斥,小师妹的嗔骂中渡过一天又一天。不过再怎样洒脱不羁也要生活,除了卖艺外武侠没有其他谋生手段,于是在繁华热闹的场所,总看到我们卖艺的身影。每次卖艺后最常说的一句话是,“各位大哥,大姐,有钱的捧个钱场,没钱的捧个人场”。钱场就是现在的打赏,人场就是转发。只是如今已是油腻的中年大叔,梦想虽在,但再也无法实现,只能寄托在网络上。于是文章就是我的武功,公众号平台就是卖艺场,每发一篇文章就是一次卖艺,每次卖完艺后都非常希望得到大家的打赏与转发,所以在这里向大家拱拱手说,“有钱的捧个钱场,没钱的捧个人场”。也许人生本是个轮回,在这里我也实现了前世卑微而又有点意思的武侠人生。
 the cours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
the cours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